“伪书”是指由后人所写而假托古人姓名的书。例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说的:“《力牧》二十二篇。六国时所作,托之力牧。”所谓的“力牧”相传是黄帝时的贤相,《力牧》这本书据说是介绍他的思想,但并非其亲笔所作,而是战国人假托的作品,所以是伪书。
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提到战国时假托的伪书还很多,有《神农》、《伊尹说》、《师旷》、《天乙》、《黄帝说》、《封胡》、《风后》、《鬼容区》等等。这些书作伪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,因为它们假托的作者年代久远,内容又过于浅陋,就好像现代人用白话文来伪造古书一样,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来。

有哪些子书是“伪书”?
唐朝时,柳宗元进一步指出《晏子春秋》可能是战国的墨者所作,不是那位春秋名臣晏婴德作品;《文子》则是一部“驳书”,通过抄录《孟子》、《管子》等书籍拼凑而成的,断非老子的弟子文子所作;《鹖冠子》可能是根据西汉人贾谊的《鵩赋》来编的;就连《论语》也不可信,因为《泰伯篇》里写到“曾子言曰:鸟之将死,其鸣也哀;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”云云。曾子比孔子小了四十六岁,到他临终之时,估计孔子已死半个世纪了,而《论语》既然记载到曾子之死,那么成书年代更该晚至战国中期。
对于《列子》一书的真伪,柳宗元正确地指出“其言魏牟、孔穿皆出列子后,不可信。”《列子》提到“列子穷,容貌有饥色。客有言之郑子阳者”,据《史记》的记载,公元前398年“郑人杀子阳”。则列子应生活在战国前期。而魏牟、孔穿都与公孙龙、赵胜生活在同一个时代,赵胜于前298年才被封为平原君,距郑子阳被杀已过去了整整100年。所以如果《列子》是列御寇本人的作品,那么就里面不该提到魏牟、孔穿、公孙龙等人。
根据柳宗元的方法,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出许多先秦子书的毛病——
其一,《墨子·所染》提到“宋康染于唐鞅、佃不礼”。宋康王、唐鞅、佃不礼死在公元前286年,距墨子生活的战国初期有100多年,这篇内容不可能出自墨翟本人之手;
其二,《商君书·更法》里称秦孝公的谥号,秦孝公死去的那年商鞅也被杀,难道《商君书》写于孝公死后,商鞅遇害之前的那段时间吗?《徠民篇》里说“王行此十年之內,諸侯将无异民,而王何为爱爵而重复乎!”秦孝公并未称王,秦惠文王称王也是在商鞅死后十三年的事,假如《商君书》是商鞅写的,他怎能说出“王行此十年之內”的话?
其三,《管子》里的《戒》和《小称》都写到管仲死后、齐国内乱之事,可知这些内容绝非管仲本人手笔;
其四,《韩非子·有度》里说:“襄王之氓社稷也,而燕以亡。”“安釐死,而魏以亡。”韩非死后八年魏国才被秦国灭亡,又过了三年,燕国才覆灭;他怎能在《韩非子》里提前预言两国的灭亡?
其五,《荀子·尧问》里写道:“今之学者,得孙卿之遗言余教,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。”所谓的“孙卿之遗言余教”显然是指荀子已经离世,才留下遗言余教。那么《荀子》难道也不是荀况写的吗?
非但子书如此,连史书也一样。《春秋》是孔子的作品,但里面却写着“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,孔丘卒”;《左传》相传是左丘明的作品,但这本书的末尾提到三晋灭知伯的事,难道左丘明在孔子死后二十多年还活着?或者《春秋》非孔子所作,《左传》也不是出自左丘明之手?——要用这样的逻辑来辩伪,那就显得幼稚了。
《史记》的作者公认是司马迁,但《史记》里有些内容记载到了司马迁死后的事,并且还抄袭了年代更晚的《汉书》!
例如《外戚世家》记载到汉昭帝时期;《齐悼惠王世家》提到“建始三年”,“建始”是汉成帝的年号;《三王世家》,里面有褚少孙的话。《张丞相列传》记载到魏相和邴吉,他们都是汉宣帝时候的人;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里更是提到“班固称曰”等等。如果据此而推论说《史记》不是司马迁的作品,那就显得糊涂了。

《道德经》也是一本伪书吗?
古代的子书和史书一般都是“驳书”,不仅并非出自一人之手,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后人修订与增补,不能简单地视为一个人的独立著作。
《管子》记载很多管仲的事迹,反映他的思想,同时又收录一些不是管仲本人所写的文章。
《墨子》是后人追述墨翟思想的书,又把《墨经》、《备城门》等各篇内容附录在后面。
《商君书》记载商鞅变法时的一些辩论场景和颁布的政令,同时又附带几篇法家的论文或奏疏。
《论语》出自有若和曾参的弟子之手,末尾又窜入一篇跟孔子言行无关的《尧曰》。
《韩非子》的《存韩篇》中从开头的“韩事秦三十余年”到“攻伐而使从者闻焉,不可悔也”都是韩非本人的说辞。而从“诏以韩客之所上书,书言韩子之未可举,下臣斯”起,后面的内容则是秦王与李斯讨论存韩观点的内容,与韩非无关。
《庄子》里的《说剑》、《列御寇》基本不会是庄周手笔。
大部分子书其实都跟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一样,具有驳杂的特色,只是学派思想明确,没有杂家那么杂乱而已。
相比于这些子书的驳杂,《老子》一书倒显得前后统一,内容矛盾极少,更可能出自一人之手。然而民国时期,却有一帮疑古的学究要对《老子》进行一番辩伪。这些人拾的也只是清人崔述在《考信录》里的牙慧,参加论战的人士有胡适之、梁启超、钱穆、冯友兰、顾颉刚等,系列文章收录在《古史辨》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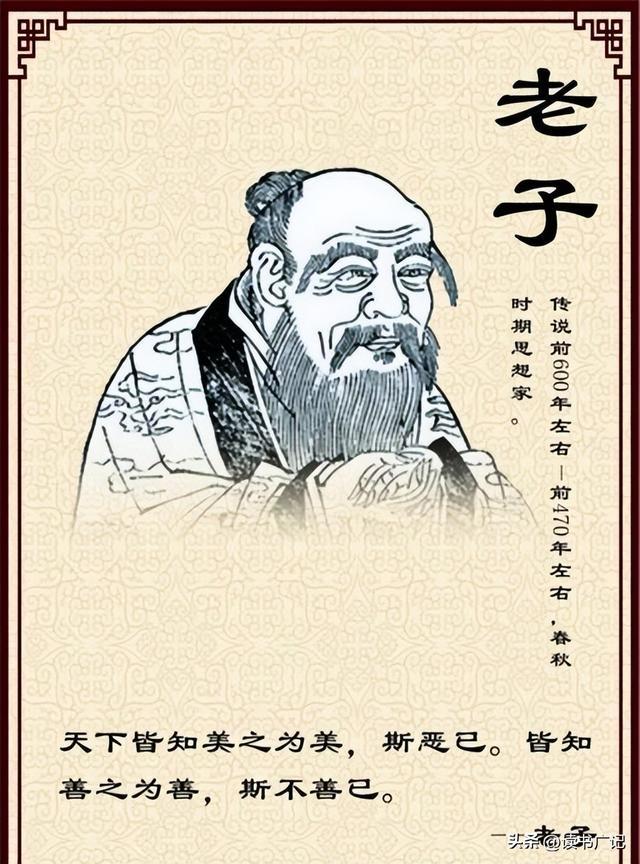
崔述较早提出老子年代靠后的观点,他说:“今《史记》之所载老聃之言,皆杨朱之说耳;其文亦似战国诸子,与《论语》《春秋传》之文绝不类也。”认为老子可能是杨朱学派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,《道德经》之于老子,就像《黄帝内经》之于黄帝、《六韬》之于姜太公一样,“必杨朱之徒所伪”,目的是虚构“孔子问礼”的传说来贬低儒家,抬高道家的地位。但是崔述忘记了,杨朱的时代是“杨墨之言盈天下”的局面——杨朱学派的对手不是儒家,而是墨家,就算要造神也应是“墨子问义”,何必编造“孔子问礼”?
民国之时,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·老子略传》里采用传统的说法,定老子年代在孔子之前。梁启超便写出《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》一文,延续崔述的路线,质疑《道德经》的年代问题,理由主要如下:
一、《史记》里的《老庄申韩列传》把老子写得扑朔迷离,简直“神话化”了,绝不可信;
二、《论语》、墨子、孟子都没提到过老子,可见没有这个人,或者年代还在后面;
三、《礼记·曾子问》里提到的老聃,像是个拘谨的人,似乎不会说出《道德经》里“民多利器,国家滋昏”那种激烈的话;
四、《道德经》文风不类春秋之时,里面的“王侯”、“王公”、“万乘”、“仁义”、“不尚贤”应是战国时候才有的。相比《论语》的浅显,《道德经》过于玄妙、深邃,应是战国后期思想发达后的产物。
对此,老子或许是战国后期的人,应当在庄周之后;要么老子还是春秋时候的人,但《老子》是战国时期托名于他的伪书。冯友兰、顾颉刚等人皆附和此论。
怀疑是对的,《史记》里的《老庄申韩列传》显然像《五帝本纪》、《龟策列传》之类一样,是从其他地方拼凑过来的,并不值得相信。但怀疑的目的应是探究、悬置判断、把教条变成相对真理,而不是妄图武断地去做另一个结论,提出更不可靠的观点——老子在庄周之后就是这样一种妄自尊大的观点,因为这个观点没有任何史料支撑,全是各种主观附会。
其次,说墨子、孟子没有提到过老子,所以老子年代要在他们的后面,这种逻辑未免过于低能。子产、蔡墨、苌弘、晏子都是春秋时代的名人,也未见墨、孟提及,难道他们都是战国后期的人?杨朱是墨家最大的论敌,《墨子》里却无一字提及他,难道杨朱也是《孟子》虚构出来的人物?或者《墨子》和《孟子》是百科全书,任何比他们年代早的人的名字都要被收录?
第三,凭《礼记·曾子问》和《道德经》短短的几千字来判定老子这个人的性格,显得太片面又自大了。《新论》反映出的桓谭是个“不读谶”的唯物主义者,然而《仙赋》偏偏又是他的手笔。难道“不读谶”的桓谭绝不能写出《仙赋》?
第四,用文风来判断一本书的年代,这是最低等、最主观的辩伪手段。照这种逻辑,那么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肯定是伪作,因为苏东坡是豪放派,断不能写出如此婉约之词。《易经》有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”、“王公设险守其国”的爻辞,《左传》有“可荐于鬼神,可羞于王公”的评论,又记载周定王队士会说:“王公立饫,则有房烝”、“夫王公诸侯之有饫也”等言辞。
《左传》又记载,诸侯伐齐时,“鲁人、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”,小国尚且请车千乘,《道德经》里提到“万乘”又有何奇怪?
至于“仁义”二字,《史记》中由余对秦穆公说:“阻法度之威,以责督於下,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於上”。《说苑》里曾子对孟敬子说:“君子修礼以仁义。”《庄子》提到“始吾以圣知之言、仁义之行为至矣。”硬要说“仁义”是《孟子》的专利,那就是死板了。
钱穆说“尚贤”是《墨子》的思想,《老子》提出“不尚贤”就是在反驳《墨子》,所以成书在《墨子》之后。然而《管子·匡君大匡》里有“尚贤于已”的说法,想必《管子》也是抄袭《墨子》了?崇尚贤才本来就是春秋时代许多人的共识,负羁对曹共公说:“爱亲明贤,政之干也。”晋文公治国理政,“昭旧族,爱亲戚,明贤良”;富辰谏周襄王要“尊贵、明贤、庸勋、长老、爱亲、礼新、亲旧。”申叔时劝楚庄王要“求贤良以翼之。”——“尚贤”思想本来就是世俗社会的共识,在钱穆眼中怎么就变成墨子的专利了?

钱穆认为《老子》既深邃又综合各派的说法,所以应出现在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之后。照这么说,那《易经》也应该出现在纳甲、《参同契》、先天图之后,因为这些理论其实都“综合”在《易经》里,而且《易经》又是那么的深邃。
究竟是《老子》影响了《庄子》,还是《庄子》影响了《老子》呢?黑格尔在《哲学史讲演录》里说,哲学是处在发展中的,最初的哲学由于概念的匮乏,会显得简略、抽象和贫乏,好像怎么解释都说得通。而晚近的哲学经过发展与丰富后,会逐渐变得具体、明确、深刻并且通俗,不仅能够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,而且还能构造出新的东西。
《老子》相比于《庄子》来说,要抽象得多了。对于“道”,它只说“吾不知其名,字之曰道,吾强为之名曰大。”这反映的就是早期哲学概念的匮乏。而到了《庄子》的《大宗师》里,对“道”的解释变得很丰富,并且有鲜明的辩证色彩——
“夫道,有情有信,无为无形;可传而不可受,可得而不可见;自本自根,未有天地,自古以固存; 神鬼神帝,生天生地;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,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,先天地生而不为久,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”
《老子》讲“绝圣弃智”,《庄子》便用《胠篋》来进行论述;《老子》讲“坚强者死之徒,柔弱者生之徒”,《庄子》便用《人间世》的寓言来通俗化这个道理;《老子》说“圣人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。”《庄子》的《德充符》便塑造出王骀这样一个“立不教,坐不议”的圣人形象。
显然,《庄子》要比《老子》更具体化,也更加通俗化。在《老子》的基本原理之上演绎出《庄子》容易,在《庄子》的基础上归纳出《老子》很难。《老子》一书不可能出现在《庄子》之后。
《古史辨》的人之所以抓住老子的年代进行辩论,只因有关老子的史料非常的少,《道德经》也不像《管子》、《墨子》那样有史实部分内容,容易分辨出后人杂糅进去的内容,因而可以满足他们书生气的争辩习气,所以才围绕着这个话题做无谓的文字之争。